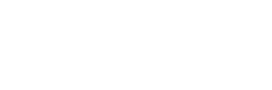哲学虽然不是讨论技术问题的常用方法,但在评估技术时,该领域的一些原则可能会很有效。举个简单的例子,波普尔在他的开创性论文《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中提到,如果一个人把认知主体从认识论中拿走,剩下的就只有信息。比如,说“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便只提供了信息。
对待信息的哲学方法很早就存在。古代哲学的主要焦点一直是事物的本质(即形而上学),这一思维方式在中世纪得以延续,但随着现代的到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重点转移到了意义(即语义)的问题上。进入信息时代后,哲学的焦点开始向技术和信息框架转移,而技术和信息框架被用来解释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后来,在中世纪,重点从这种美德伦理转向宗教形而上学。后来,在现代时期,康德认为伦理学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完整描述的基础上的。如今,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伦理话语需要从信息的角度出发。从事物的终极本质来看,人们会意识到,无论我们的论述是形而上学的、逻辑学的、理性的,还是认识论的,伦理始终是智力旅程的终点。
信息伦理和哲学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对我们处理今天的日常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搜索引擎带来的“被遗忘权”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已成指数级增长,仅仅通过删除某些链接来减少问题将造成更大的问题。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当今的技术问题,我们需要明确问题的核心是隐私权和话语权这两大伦理原则的冲突。
使用康德的方法,我们可以将来自外部世界的消息(又名消息源)称为数据。信息受数据的限制。世界并不完全建立在我们的想象之上,也不像通过我们的感官所呈现的那样。数据和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应该从表示的角度来理解,而且应该从提供的角度来理解。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获得了理解数据并将其转换为正确信息的方法。如果把知识等同于现实本身,那就太天真了。虽然现实是信号的来源,但我们的知识只是信号。换句话说,收音机发出的音乐并不代表收音机本身。
流行的图灵测试也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机器是否会思考这个问题不值得讨论,因为我们不能确切地定义什么是思考,什么是机器。然而,一旦测试运行,就可以看到个人和机器的不同反应。根据图灵的说法,为了找到对思考机器的响应,需要明确抽象的层次。与其他可能有不同抽象级别的领域相比,计算机科学领域基于参与者不同级别的能力来定义这种抽象级别,以便理解问题并对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响应。
在过去,权力指的是在生产新商品的意义上创造或控制事物。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权力不再是指商品的生产,而是指服务或经验的生产。对信息控制的需要导致了这一转变。毫不奇怪,政府正从对事物行使权力的意愿转向对信息行使权力的意愿,这也改变了有关事物的信息的性质。换句话说,那些控制问题的人也会影响回答。作为公民,我们一旦理解了这种新的权力,我们也可以开始相应地管理信息,并增强我们自己的力量。
【数字叙事 原文:Ayse Kok;编译:黎雾】